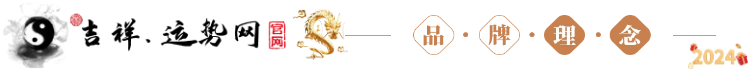《中德文学对话中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冯晓春著,科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231页,108.00元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发现众多掷地有声的作家名字,而这些作家又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即双管齐下、著译并举。在现代翻译文学作品中,自然是英语文学拔得头筹,毕竟英语自晚清以来就是中国传播最广、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因为毗邻和同文之便,东瀛成为诸多现代作家的留学目的地,而日本文学也相应地成为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对象;法语文学因其浪漫、优雅、迷人的特质吸引了一众作家,尤其是留法勤工俭学作家的青睐。至于充满诗性和哲思、同样异彩纷呈的德语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印迹也不可谓不深,尤其是从中走出了鲁迅所言“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以及“战国策派”核心人物、剧作家陈铨。考察现代作家的德文习得路径和德语文学资源出处,无外乎三种情况:要么在负笈日本时顺带习得德语、接触德语文学,比如郭沫若、郁达夫等;或者在留德时浸润了诗哲之国文学的风雨,比如前述冯至、陈铨等;抑或并无负笈他国的体验,却在国内接触了德语语言和文学,比如曾求学于水木清华的李长之等。
检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德语文学有渊源者,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都是须眉。正如冯晓春的学术专著《中德文学对话中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所言,这自然跟中国现代女作家在主流视野中的“缺位”不无关系;如果再仔细爬剔梳理中德文学关系上的中国才女,更会发现这一“缺位”现象越发严重,专治德语学科者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扼腕长叹,缘何“以德为师”“与德对话”的现代女作家如此稀少,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姑且不论张爱玲、苏青、丁玲、苏雪林等进入大众视线的著名女作家多与英美或法国文学颇有渊源,而与德语文学几无关联;就算是那些有着留学或游学德语国家的女性文化学人,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与德语文学擦肩而过:早期留德医学女博士、文学研究会会员张近芬有多部译作问世,但她翻译的是英国、法国、日本乃至丹麦文学;中国近代女性运动先驱吕碧城被赞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曾游历维也纳、苏黎世等德语区历史文化名城的她也留下了大量游记文字,不过,这位与秋瑾并称为“女子双侠”的女中豪杰关注的多是政治、经济、社会、民生乃至动物生态保护等上层领域的话题,对德语文学几乎不置一词。在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惟其珍稀,而愈显弥足珍贵。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作者在新文化史理论和性别研究视角的启发下,从文学和文化交流的三重模式出发,挖掘中国现代女作家创作中的德语文学因子,呈现她们参与中德文学对话的过程及其带来的影响效果。

维也纳之吕碧城
在引入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和理论启示之后,作者在著作主体部分的第四章到第八章展开了绵密而扎实的个案研究。第四章专门探讨歌德的成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与四位女作家(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谢冰莹)的紧密关联。这四位女作家都算得上是歌德书信体小说的知音,在其爱情书写和创作中“如盐化水,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充满青春迷惘和感伤主义的“维特元素”,甚至仿照这一体裁创作了大量的书信体小说,其中的“驿寄梅花,鱼传尺素”演绎出一段段浪漫而多情的恋爱故事。谢冰莹甚至把这一小说投射到现实生活之中,称自己的恋人为“维特”或者“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对《维特》的接受多流于扁平化乃至流俗化的层面,歌德笔下更加微言大义的主题,诸如现实映射、社会批判和文化诉求等,经常被三角恋悲剧这样的表象故事遮蔽。不过,在谢冰莹身上也可窥见“《维特》影响的另一种维度”:短短几年以后,当初沉湎于伤感爱情故事的谢冰莹果断告别了恋爱至上的美丽梦境,义无反顾地转向革命,这生动地体现了歌德原著折射的“时代精神的变迁”(80–82页)。除了《维特》,五四时期的另一部德国文学名著《茵梦湖》也吸引了庐隐和石评梅两位女作家关注的目光,为此作者专辟第五章展开研究。庐隐在《象牙戒指》中从全知视角出发,以石评梅与高君宇这位“红色恋人”的爱情纠葛为蓝本,进一步强化了《茵梦湖》中“独葬荒丘”的悲情苦恋意象。与之相对的是,石评梅则在“革命加恋爱”的自传式书写中一方面赓续了中国文学古已有之的感伤主义传统,并从《茵梦湖》中汲取相关养分进而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通过从“独葬荒丘”到“合葬荒丘”这一个字眼的变异塑造了一个成为自己悲剧的主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新型知识女性形象(102–103页),进而演绎出《茵梦湖》在中国现代文坛接受史上的一段精神史的变异。
都说德国是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或曰“诗思之国”“诗哲之国”,这里的“诗”(Dichtung)自然是广义上的文学创作,但理所当然地包含狭义上的诗歌在内,何况包括德国在内的德语区诞生的举世闻名的诗人可谓灿若群星。在这星汉灿烂的诗之苍穹,也有几颗熠熠闪光的星辰在几位中国现代女作家那里找到了知音:古典主义的歌德、从浪漫主义转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海涅、还有以咏物诗名扬天下的象征主义代表人物里尔克。专著第六章聚焦这一研究对象,首先探讨了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和九叶派诗人代表郑敏与歌德诗章之间的文学因缘,接着转而讨论上文多次做过个案研究的石评梅在散文写作中对海涅后期政治抒情诗《颂歌》(Hymnus)的借用,最后探讨以陈敬容和郑敏为代表的九叶派女诗人对里尔克物诗(Dingedicht)的追随,以及对他的艺术观念和生命思考的借鉴和化用。如前所述,德国文学原本就以深刻向内、发人深省的思辨见长,跟哲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特别卓尔不群的德国作家或哲学家对“诗哲型立”这顶桂冠可谓当之无愧,比如歌德、荷尔德林、尼采、海德格尔等。(叶隽《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的现代中国接受为中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页)有鉴如此,作者接下来揭橥现代女作家与德国哲学,尤其是意志哲学之间的因缘,也就水到渠成。无论是庐隐对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进行回炉再造,还是冰心在“超人三部曲”(小说《超人》《烦闷》《悟》)中以“爱的哲学”超克尼采的“超人”哲学,抑或袁昌英通过引介、翻译、阐释、评论和创作等多种方式持续关注弗洛伊德学说,无不体现了德国意志哲学在中国现代女性的心灵书写中留下的印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如作者所言,这也可以部分解释缘何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理性主义哲学家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群体中几无知音。(174页)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啻一部翻译史,而留学史也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故而专著第八章呈现了这三者之间的契合点,掘发了虽然不以作家名世、但有重要著述留存、而且有着负笈德国经历的女革命家胡兰畦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此外还论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作家的德语文学译介成就,同时提及近现代中国留德史上寥寥无几的女性学人,并认为理应对这一女性代表人数的不足抱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著作随后总结了现代女作家在中德文学对话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点,并从性别审美差异的角度归纳出深受“主情主义”影响的女作家接受德语文学的几个表征,比如关注自身生存境遇,尤其是将理性思辨至上的形而上的德国哲学纳入形而下的、相对隐秘的情感范畴(大有“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之意),并从阅读效应的角度出发,不无见地地指出“阅读即道路,是女性走向文本、走向自我、走向世界的道路”。(200–201页,206页)当中国近现代女性被时代和社会的客观条件锁上了负笈留学和习得外语这些大门的同时,冥冥之中又被推开了阅读这扇窗户,而德语诗哲作品的汉译无疑是透过这扇明净之窗窥见的最美风景线之一。
本著作内容详实、论述颇有深度、中外文参考文献丰富,附录的人名索引给读者提供了较大便利。而其最出彩处,在我看来,则是让学界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话题,即现代女作家与德语文学之间的对话浮出水面,并倾尽全力收罗了几乎是所能找到的一切边角材料,让现代中国文坛上为数不多的“以德为师”“与德对话”的女性作家的身影及其著译作品进一步明晰化、鲜活化、立体化。本著作诞生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也可以窥见专家代表和国家层面对这一研究主题的首肯和嘉许。对于同为德语学科学人的我,尤为看重的仍是作者的学科关怀、学科自觉以及自省意识,即我们这个学科能为当今国内学术界做什么,简洁点说就是“德语学科何为”。就文学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毋庸置疑的是,继续翻译和研究德语文学本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语文学阐释学一直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但另一方面,探寻中德文学之间存在的可能关系和因缘,挖掘两者之间包括翻译、转述、以借鉴和袭用为关键词的仿作、“创造性叛逆”式的改写或曰变异、乃至跨媒介和多模态的移植和改编等等,在我看来,同样也是德语学科学者能够而且应该努力耕耘的学术领地。尤其是在“重写文学史”,构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学的呼声中,本书展示的一些主流现代作家与包括德语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之间的因缘际会,以及一些相对边缘的作家(比如创造社作家段可情、文学研究会成员赵伯颜和唐性天等)与德语文学结下的不解之缘,都可以给我们提供丰富而多元的精神资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女作家与德语文学之间的关系,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中德文学关系,都并非单轨,而是一条双向道。就女性写作而言,不管是在德国还是中国,早期似乎都不被人看好:德国作家博尔曼(Stefan Bollmann,1958—)甚至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写作的女人危险》(Frauen, die Schreiben, leben gefährlich);至于在中国古代,由于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女性写作更是被忽视和掩盖。尽管如此,早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笔下,就可窥见他致敬中国女性诗人的痕迹——他如此珍爱那些在当时并不入流的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以至于他在手稿中划掉了之前写的“中国诗人”,而改为刻意强调她们性别特征的“中国女诗人”。(谭渊《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145–146页)自汉学在德国姗姗来迟、然而后来居上以来,该学科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这就包括对本著作中研究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翻译和研究。而就中国现代女作家对德语文学的接受与德国汉学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译介这一双向关系而论,又可以瞥见时有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比如本书未曾提到被誉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薄命天才女作家萧红,因为目前暂未发现她与德语文学之间的联系,但迄今德语区已经出现多个萧红作品的译本(孙国亮等《上海文学海外译介传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143–153页),《呼兰河传》德译本还在2024年再版。这一不平衡的接受状况,也可以视为由本著作延宕开去的研究展望之一。

萧红
最后要说的是,专著中偶尔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些许可以进一步完善之处。有关陈敬容翻译的里尔克诗歌,作者未能追索出《青春的梦》《回想前生》《遗诗》三首的原诗(124–125页),其实分别为《图像集》(Das Buch der Bilder)中的《男孩》(„Der Knabe“,首句是Ich möchte einer werden so wie die),同样收入《图像集》中的《回忆》(„Erinnerung“,首句是Und du wartest, erwartest das Eine),以及收入《1910–1922年诗歌》(Die Gedichte 1910 bis 1922)的《你这预先就……》(„Du im Voraus“,首句是Du im Voraus verlorne Geliebte, Nimmergekommene)。就材料和史实而论,作者已经做了最大程度上的挖掘和搜集,但偶有遗珠之憾。专著里曾做过个案研究的冰心,因其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身份与《格林童话》很可能存在关联。冰心曾说:“我接触到当时为儿童写的文学作品,是在我十岁左右。我的舅舅从上海买到的几本小书,如《无猫国》《大拇指》等,其中我尤其喜欢《大拇指》,我觉得那个小人儿,十分灵巧可爱,我还讲给弟弟们和小朋友们听,他们都很喜爱这个故事。
”因此,冰心作品是否跟《格林童话》之间存在更深层次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事实上,这一点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则期待后学。本书还提到曾经负笈东瀛的知名女性作家沉樱(原名陈瑛,1907–1988)与德语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183–184页),但有些史实还需进一步稽考和查证。比如作者引用二手资料说20世纪20年代沉樱曾与洪深合作翻译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怀疑这个版本当是由洪深与同为剧作家的马彦祥合译(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因沉樱与马彦祥曾经结为伉俪,故而有此误会。沉樱所译茨威格的《同情的罪》,题名取自其英文译名(Beware of Pity),现在一般译为《心灵的焦灼》(Ungeduld des Herzens)。她翻译的黑塞的《拉丁学生》收录了五篇作品,但不一定全是小说,因为涉及两封书信;另外《大理石坊》今日一般译为《大理石的传说》(Die Marmorsäge),《求学的日子》原名为Unterbrochene Schulstunde。沉樱所译富凯的《婀婷》(Undine)其实也曾在大陆出版,收入译文合集《女性三部曲》(重庆出版社,1982年)。沉樱翻译的茨威格和黑塞作品至今仍在台湾地区不断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她的德语文学翻译及其与创作之间的可能性的关联,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个案。
总之,从中德文学关系的大框架出发,挖掘德语文学镜像和资源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发,乃至现代中国的精神塑造和文化构建,值得包括国内德语学科在内的国内外学术界继续挖掘和探究,而这本《中德文学对话中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积极而有益的参考和启发。
西南交通大学 何俊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