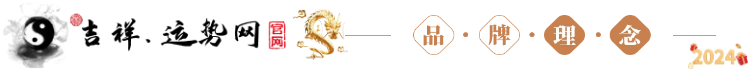第十九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至暗时刻
张译文
(理学院 应用化学专业 2019级本科生)
注:本篇为病毒学和传染病学的学科拟人,人物形象来自笔者的一位友人,背景为现在的疫情,大概是在一月末二月初的某一天,两人都来到了武汉协助处理疫情,两个人住在酒店。
一
传染病学戴上矿工灯,调整好系带后上下晃了晃头以确认它不会从头上滑脱或箍得太紧。被过滤器筛过的空气携起水雾从细密的孔流出,一呼一吸间他能听到像是疾风钻过窄缝时叫出的嘶鸣。他四散的目光聚集至面前洞口时扫过身旁一条贴着草叶匆匆爬走的蛇[①]。他扶住岩石的干洁处向洞口内探步,抬起手臂时手掌擦过岩石上覆着的苔藓,湿滑感隔着防护服手套传来一瞬。
随着传染病学往里走,他的视野伴洞穴内部空间一并开阔起来。橡胶靴踩在泥地上,把猴子和田鼠的脚印重塑成靴底的锯齿状花纹,把风化后干燥的动物粪便压扁。他在几个岔口的汇聚处停下,拿出被防水袋密封的地图,读过上面的字迹后走进其中一个。
洞口溪水绕红木和罗汉松汩汩流动的声音和阳光被他逐渐抛在身后。传染病学侧身躲过碎石堆,避免洞壁的针状结晶体扎上防护服,小心翼翼地爬下一小段缓坡。黑压压的洞顶映入眼帘时他眯起眼仔细分辨了一会儿,而后发出一声短促的“啊”,声线因兴奋和紧张而绷紧如弓弦。对,就是你们,他想,这次灾祸嫌疑最大的、病毒的源头……
不知是灯光还是声音惊扰了感官敏锐的蝙蝠,它们松开洞顶,刚要下坠便展开双翼从传染病学的头顶和肩旁飞过,浅灰色、灰棕色和棕红色被翼膜的黑色抹成含混的一片晦暗。多亏呼吸面具,他的嗅觉不必受到蝙蝠及其粪便味道的侵略,但那滞涩如生锈的齿轮一齿一齿啮合和清洗水箱时橡胶手套和玻璃间的薄层水膜被挤压时的咯咯声在洞内经回返层叠而放大,已足够让他头皮发麻,上下牙死死咬在一起。忽然,这集群中的一只平齐他双眼斜斜飞来,角度似是对准他的额头,好像下一秒就要撞上他的灯。传染病学本能地闭上眼,退一步,后倾上身——
二
传染病学发现身边人群涌动如海潮,而裹挟在其中的他被挤着推着,头脑混乱。他盯着一侧摊位上的鱼、虾和贝类看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个海鲜市场。“尽快离开”的想法在他思维道路上横行,使他无暇思索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嘴里连连说着“抱歉”,从人潮的中间挤到边上,却在下一刻就被人拽住了衣服:一个中年男人,身旁立了块牌子,摊位摆得比其他人的都低,冰块上稀疏地摆着几条鱼。他瞟了眼熙攘的人群,把牌子翻过来放在传染病学眼下,谄笑着,神色里却有那么一点神秘,挡不住地流露出来。
“帅哥,来瞧瞧,你肯定没见过……”
男人弯腰从地上的泡沫箱里掏出什么东西,不等传染病学发话就借着塞进他手里。那一刻传染病学颇有些恍神,他的手指颤了颤:光滑、有软骨一样的构造;覆有柔软的短毛;和身量相比略大的耳朵。
传染病学只觉得全身沸热的血轰地冲上前额,心率跳出正常的范围,向着过速的极限急升。它怎么会出现在海鲜市场?它应该在昏暗的洞穴或废弃隧道里,倒着挂在钟乳石之间或顶壁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人抓在手里——
他摊开手,蝙蝠的双翼舒展开,带着那人类鲜少涉足之处藏起的深重而尖刻的黑,肉眼可见地变宽变长,越过他的躯干在他的头顶交织。豆大的眼睛和马蹄形鼻叶下缘拼凑成一个丑陋的笑[②]——
三
“……喂,醒醒。”
朦胧间传染病学听到好像有人叫他;一只手扯了两下他的耳朵。他勉力抬起昏昏沉沉的脑袋,掀起眼皮瞥了一眼:拎着酒精喷雾的病毒学。后者盯着面前被自己叫醒——也可能是从梦中惊醒——的人把蹭在胳膊上的纸张按下,戏谑语气夹着丝丝担忧的杂质:“克拉伦斯,你刚才眉头间的褶皱堆得像山谷和山脊。你梦到什么了?呼吸困难的自己费力吸着氧气?”
传染病学揉揉眼睛,长吐一口气,这才感觉偏离去山洞和海鲜市场的意识回到了正轨。圆形吸顶灯和石膏线上一排边灯亮着,落入彼此的昏黄色和月白色像是一大勺蜂蜜完美均匀地溶进温水,让人错觉这甜味也能渗进梦里。在暖光下对着草纸苦思冥想却沉入睡眠实不怪他,且他险些在梦里和蝙蝠亲密接触,这是多么可怕的噩梦;这一觉睡得远远称不上好。他扶着前额,手指越过发际线插进发根间,“比那可怕一万倍。我连着做了两个噩梦,先是梦见我一个人穿着全套装备进山洞找蝙蝠,一只蝙蝠对着我头上的灯就撞过来,又梦见我在一个海鲜市场,被人拽着往手里塞了一只蝙蝠,就是我们怀疑的那种。”
“你没去够奇塔姆洞?还想埃尔贡山[③]一日游?”
“我记得你也梦见过猴子拿针头指着你,杜克。几点了?”
没得到回复的传染病学只好拿起手机。二十三点。他揉着因硌着桌子而隐隐作痛的颧骨,问病毒学,“你们今天怎么样?”
“他们从粪便和肛拭子里检出了小东西的核酸,”病毒学拧开矿泉水瓶喝了几口,捏得薄层塑料的瓶身咔啦响,“做了接种,等潜伏期过去的原代培养和传代培养,试试能不能分离出小东西。明天你就能读到提醒注意粪-口传播风险的新闻了[④]。你今天的R0[⑤]?”
“不是我的R0,是你那小东西的R0。好消息是,这两天发病期的下降了一点。然而,这个病毒潜伏期长,症状不明显,前几周检测效率低,还缺少必要的隔离措施,那段时间公布的确诊人数比真实值低了不知道多少,直到——”
病毒学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不想听传染病学滔滔不绝地和他讲这些。浅海在冲上深色血痕前便知趣地退潮,“总体来讲,我们估计两周后才会迎来感染人数的峰值。这个很清楚,很好,但我现在苦恼的不是它。”
传染病学从椅子上站起来,靠在桌旁待眩晕感随着眼前发黑的几秒一起消失后,抹着桌面拿起刚才被他无心垫在脸下的纸,那上面散乱地写满了字,有的字被描了几遍,整个加粗加大了一号,还被框定在交叉的短直线或圆圈里;有的字被粗暴地划去。每一个字都易于理解,可当它们手拉手躺在同一片地方时,表意就好像自纸上蒸发后在他人的思维表面凝结成了水气,模糊得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写下它们的人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活动着因久坐而发凉的小腿,一边念念有词,“第三例去疫源地接触过高热患者,可这个高热患者并没有被诊断是新型肺炎的患者。难道是她引起了百货大楼里的传播?可根据时间我们不能建立第三例传染给第一例的流行病学联系……”病毒学猜他在这个节点冥思苦想了至少一晚上,对方双眉拧在一起的趋势不比刚才做噩梦时弱许多,“第四例也去过存在本地传播的隔壁市,和第一例、第三例都在这栋百货大楼里工作,但她们平时没有任何联系和交集,也没有可以共同就餐的食堂,甚至没去过公共卫生间。”
他顿住脚步,全然没注意到这张饱经摧残的可怜的纸被他捏出了折痕,“线索到这里就断了,你说她们为什么会构成传染链呢?[⑥]”
回应他的是一阵喀嚓声,它将泡在眼下难题迷雾里的传染病学从思索里拎出来。他扭头,见双腿大张坐在床沿的病毒学嚼着东西,颇为惊讶地睁大了双眼。病毒学颠一下袋子,伸过去,“吃吗?”
“我已经刷牙了。”传染病学凑过去,看清里面是油炸薯条后,上扬的语调将出口的陈述句硬生生扭出疑问语气,“我记得你不吃夜宵?”
病毒学摊手,“晚饭吃了一半就被叫走,等我回到休息室的时候它已经凉透了。没吃饱。而且,不好吃。”他迅速解决掉一整袋膨化食品,把包装袋叠了两下丢进垃圾桶,“这次吃不到热干面了。”
传染病学没回应他,放任脚步声代替沉寂的话音填充两人间安静的空气。他停在条件与结果间的断路上踟蹰不前;以现在掌握的信息,追求缜密的他再怎么捋顺环环相扣的链条也不能强行跳过一节直接把二者连成完满的圆环。于是他索性撂下纸,想着要放松一下眼睛,走到窗前拉开闭合的棕色窗帘,双手撑在窗台上,俯瞰这座深陷疫情泥潭的城市的一角。
阴云冷酷地拦下月亮投向人们的柔和目光,拖着绛紫色的背影缓缓地向远方漂动。本应闪烁着叫嚣着的霓虹灯和车灯都缄默不言,斜对面药房的牌匾就是这条街上唯一的光源,透过夜色蒙纱的冷白光闪着幽幽的蓝。树影投在窗户上,千回百转的曲折边缘稍作改动便可印出这座城市的轮廓。电线杆间架起一座座电缆的弯桥,在这个街上面对面交流与欢笑被病毒切得粉碎的时刻,它们将每一片狭小的空间牵在一起,无数无关的人借着它们彼此倾听与诉说,他们重叠的心跳声推动这只蝴蝶[⑦]在波涛起伏的江上舞动。
“客观说,这次肺炎传染性强而致死性弱,相比之下问题不是特别大。每天时刻关注情况,眼睁睁看着数据不停地上涨,我能感受到最近我的情绪越来越平缓,甚至于,”他顿了一下,语速忽地加快,“像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但一想到那是一条条被系在我们和病毒之间绳子上的人命,等着我们把他们从死神手下抢回来,想到在我们照不到的阴影里,多少人因为医疗资源紧缺,跑遍了医院后走投无路,被迫在家里死去,多少人惜命却不得不为生活四处奔波,我还是,我……”
他不再说下去。情绪的疾风推着夜下的浅海泛起浪花。
病毒学站到他身边,望着黑洞洞的街道,天幕浮在沥青马路蓄积的水洼上,没有鞋子与车轮的倒象比一触即碎的镜子更不真实。“在病毒面前,不分个体,只分种族。人的千姿百态在疫情下一览无遗。这群蠢货总是以万物的灵长自称,狂妄自大到无视自然法则;可祸端从来都不是什么其他的物种,而正是打开魔盒的他们自己。”
“十七年前他们已经历过一次,不吸取教训,现在才明白人类从来不应如此自大。这是自然给人类的教训和惩罚,也是他们应为自负付出的代价。”他的目光冰凉地落在传染病学脸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纵容他们,为什么要制止这种有效的教育措施。”
“至少这次他们中又有一部分学会了,这不是好事吗?”
两人都清楚,自己与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传染病学背负着医科的责任感,视医德为他存在于世的基石,珍视每一条人类生命,以消灭病原体为行进的终点;病毒学怀着生科对自然纯粹热烈的好奇心,全神投入于纳米级的粒子,注重整个群体的生存与覆灭,对人类生命的态度飘忽不定、暧昧不清。大部分时间,他们处在彼此的对立面上,起点极为相近,却把眼睛看向不同的星星,渐行渐远;然而,偶尔他们也会走到一起,像现在这样在同一个房间里讨论同一场疫情,备着明天向共同的敌人进军挥剑。在以百年为计算单位的时间长轴上,他们的目光会交汇于这一个小小的点。
四
传染病学的手机震了一下。他点开,回复完流行病学和疾控中心专家组的消息后扫到屏幕右上角的时间,才后知后觉睡意已袭卷而来,他打哈欠拖出的长音让病毒学侧目。
“还不睡,你明天要不要精神去推理了?我期待你在报告会上睡着的英姿。”
“因为你的小东西太麻烦,像你一样。”习惯了那嘲讽语气的传染病学和往常一样反击对方,“祝你明天起晚,赶不上早饭。我现在就睡。”
病毒学回他一个恶狠狠的眼神,替他按下顶灯的开关。传染病学钻进被窝,直愣愣地盯着那枚无光的满月。现在黯淡,但不久就会重亮的,他想。卫生间传来的水声滴在他的耳膜上,白噪音似的,使他的上下眼睫忍不住纠缠在一起。他在昏黄的光下闭上眼睛。
[①] 之前有新闻报道称蛇是新型病毒的中间宿主。
[②] 以上关于蝙蝠的描写写的全是中华菊头蝠。
[③] 奇塔姆洞位于埃尔贡山,感染马尔堡病毒的一名病患曾进过这个洞穴,有可能是在这里感染上了马尔堡病毒。
[④] 引号里病毒学说的话来自我根据“病毒可能存在粪-口传播”的新闻与相关资料的猜测。
[⑤] 基本传染数是在流行病学上,指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通常被写成为R0。
[⑥] 这里说的是之前天津宝坻区某百货大楼的五个病例。
[⑦] 武汉市的轮廓像一只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