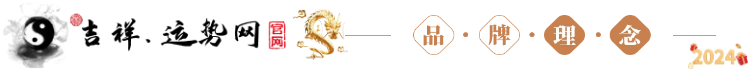转载自《鹦山山居》公众号,为九月九日上午十点在泉州三中旁的鹦哥山旁小屋,鲤城区西边巷35号的关于此书的读书会

《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初版是1999年王铭铭的《逝去的繁荣》,这是一部关于泉州历史的人类学考察著作。该书以泉州城为主线,叙述了唐宋至明清时期由逐渐繁荣--繁荣--繁荣逝去这一过程,折射出泉州城地理、历史、文化信仰、政治等方面的历史特性与时代特征,是一本书无论从内容还是视角上看,都值得反复品读的书。
五代留丛效扩城以后,环城种满了刺桐,所以泉州有了“刺桐城”的别号。“刺桐”生长力旺盛,花的颜色鲜艳,留从效扩建城市后种植刺桐是有多方考虑的,例如和宗教、自然环境以及刺桐花的寓意。该书再版取名“刺桐城”,以“刺桐”这个代表了持恒与绽放对立统一的意象来隐喻泉州城市史的总体特征,而“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则是对内容的总体概括。
“刺桐城”是泉州的三个别称之一。另外两个是“温陵”和“鲤城”。“温陵”和“泉州”的来源时期相近,但是在宋代更加流行。“鲤城”这个别称是在1352年元朝的时候契玉立拆除罗城南墙,扩张版图,因形状与鲤鱼相似,所以在元朝或者之后就有“鲤城”这个昵称。关于这个名称还存在风水宇宙论的研究:小东门是鲤鱼嘴,在正东方,日出的地方,新、西交界的地方是鱼尾,新门在正西,是日落的地方,那有鲤鱼戏珠、鲤鱼跃龙门的寓意,也象征着地方的活力。
“泉州”的名字是得名于清源山的虎乳泉。泉山和泉州的名字由来都是来自这个泉水。山的泉水对于地方的滋养,就是“泉州”这个名称所指。
此次读书会研读了前六章。在再版自序中,作者总结引起学界关注的归结为两类,一类是明朝以前汇合到此的各种异域文化,还有一类是发自本土的汉人民间文化。
异域文化因素是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关注的,张星烺先生在1929年的《中世纪泉州状况》提到泉州从唐末历经五代直到到北宋,繁盛的程度与逐渐广州并列,界定了泉州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1926年张星烺和陈万里等一行人到泉州访古,对宋元泉州与海外各国交通贸易的盛景以及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对泉州的记述进行梳理,写出《泉州访古记》一文。除了这次访古,之后的调研还进行过两次。一行人中专攻的是文史、神话和民俗的学者顾颉刚,根据自己关注的是民间文化,经过几次的调查写了《泉州的土地神》、《天后》两篇文章。他在访古时发现,泉州人对铺镜神明有很深的信仰,分立的公庙和祀神还联结为“东佛”和“西佛”两大党派,甚至迎神赛会时还有械斗现象(第七章中都有详细的阐述)。铺镜神数量很多,有来自民间传说,但多数是周边神祀的模仿。上古时期的“社”承担着祭祀的作用,配祀有功德的贤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和社神都有专属的称号,使得原有侍奉贤人的职能消失,贤人另立专祠。后来民众觉得福德正神的神力弱,就会将土地庙依附在其他神明旁。这里举出表现“土地神”祭祀的杂乱现象的例子:奏魁宫“土地庙”里收藏的“天使石像”,被人焚香祭祀,信以为有灵。这样的现象如何去解释说明也为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者们访古不久,吴文良的泉州古代外来宗教石刻研究、吴藻汀的泉州民间传说研究,再次为泉州塑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是世界中的泉州,一个是自在中国的“民俗泉州”。在汪毅夫、洪峻峰、张帆、王铭铭的文章发表之前,张星烺、顾颉刚等人对泉州的研究没有的到充分的关注和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庄为玑、陈垂成、林胜利的文史书籍先后印行,将泉州文史研究带入不同的时代。张星烺、吴文良、庄为玑重宋元轻明清、重海交轻民俗;顾颉刚、吴藻汀等是重明清近代轻宋元、重民俗轻海交。作者受几位前辈的启发,但也认为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探索。

“汉学人类学”与泉州所在的闽南语文化区渊源极深。荷兰汉学家高延19世纪末在闽南地区展开“汉人”宗教的民族志调查,开创了西方人类学的先河。在“燕京学派”奠基者引领的社区研究时代过后十多年,20世纪50-80年代,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和实地研究再次转回东南。而这些研究者并没有顾及像顾颉刚、吴藻汀等前辈的文化研究,像伦敦的费里德曼将东南家族载入西方人类学史册,他的晚辈通过台湾的乡村和香港的新界去窥视中国的家族、祖先崇拜和民间宗教。
在前部分回顾了泉州研究的学术史,这些研究展现了泉州是一个既有思想“亚传统”,又有“关系千万重”的地方。泉州所蕴含的内涵,不仅是各种加冕名号和历史信仰的简单相加,而是前述二者在其他环节的糅合下共同构成的复合人文世界。
《刺桐城》的论述重点在于“今古之变”这两个端点之间的漫长中间阶段上。基于“城”、“市”双重性的结构诠释,一方面强调这种双重性的恒定,另一面呈现“市”(贸易、流动)与“城”(防卫、绥靖)两种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
书中的“刺桐城故事”以历史为轴,简单概述不同朝代的政治形态、民族关系,描绘了宋元时期的繁盛之境:官方圈地扩大海外贸易,海贸发达,与外国交流渐多,国外的传教士多在这一时期随海外贸易船队来泉州,泉州的包容性使得地方特色文化将外国宗教文化很好融合,形成了泉州多元文化特点。但因为融合了国外文化,所以这又带有世界的属性。边陲的拓殖、海上的交通发达、官府的运营都让泉州的经济和文化繁盛而到了清朝的海禁,相关封闭化趋势的增强以及城市开放性程度的下降成为了“内在的异类”。所以在清初、清末到20世纪,一些相关的殖民战争、运动等都无法改变泉州开放和封闭两方面同时遭受通商口岸冲击的命运。这部分是对二三四章的脉络梳理。
引论
关于泉州,中国学界关注点似乎集中在古代泉州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之限度问题上,这里举了一个1997年《光之城》这部著作的例子。这部著作记录了雅各1271年到达到泉州的见闻,当初已经分化为接近自由派和文化守成派两个阵营,这本书让人更关注的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国馆观存在的差异。实际上,令欧洲国家最难以相信的是,远东在文艺复兴之前早已有了种族和文化兼收并蓄的面貌,也有了重商与抑末的政治经济思想辩论。
作者探讨了文化的概念。一个是欧洲国家营造出的一种文化认同感以及利用文化来创造金钱的内部资本主义发展手段。另一个是成为殖民扩张的对象。文化一词的广泛运用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有关,西方社会的专家们难以想象非西方社会也有文明史,所以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将一些愚昧、蛮荒、古代的社会和近代的欧洲相比较,来确立自己的帝国主义自信心。要理解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概念的关注,不能脱离这一语境。中国在与近代西方势力接触以前,倾向于把自己的国土想象成一个世界,形容这个世界为“天下”,19世纪末以后,为了抵制外来影响,就通过类似于像欧洲的想象来营造民族的历史认同。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两个关注点,简单说来一个是整体的中国文化,一个是与外来文化对比的差异。泉州古代的开放而引发的辩论的文化政治成因。
“文化”概念与权力有着密切联系,现存的文化理论多注重权利的揭示,比如运用文化符号来营造社会关系。但是文化本身是不断运动的,是不同的因素之间的互动和结合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不能说强制的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文化加之于人事物中,因此其实有很多主流观念是脱离了人和社会提出的,忽略了民族精神的真正含义。开篇揭示出泉州古代开放式辩论的文化政治成因。
作者总结了泉州有三条主要的年度周期仪式。一套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颁布的法定节假日,久而久之成为了“休息日”;第二套是周期性的“艺术节”,这是属于,是在政府安排下的地方文化官方活动;第三套,是民间的仪式活动,他们以家庭为核心,被政府视为迷信活动,它其实承载着一种历史的观念,主要集中于人和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家族和社区。国家的仪式试图推导的是民族的命运,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控;地方政府则是彰显地方过去推导未来的繁荣;民间则是以小单位或者以个体为主去寻求生活顺遂。年度周期仪式就是历史、文化、权力的结合,或者说是不同的权力通过选择历史来选择文化的结果。从生活史的角度看,这三套仪式是相互指责的关系。国家和地方政府把民间仪式看作是文化残馀,而民间则对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官方仪式呈冷漠态度,当然,休息日大多只是作为劳作应有的放松自己的特定节日,并没有太多精神上的追求,他们认为能够庇佑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祖先和地方神。其实,历史、文化、权力是互动又冲突的,各个方面的转向能让我们更好的反思和运用这层关系去解读一些真正趋近于历史的本质。当然,泉州普渡、例如祁风仪式的废除等等,许多政府施压的移风易俗导致地方信仰的减弱,甚至也许在未来日渐式微。除了感慨于官方限制,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创新也使继承者们主动的去忽视这一系列的行为。
边陲世界的拓殖
第二章“历史的场景”对泉州的地理位置、人口演变、行政建制、地方特点以及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略作介绍。第三章“边陲世界的拓殖”展现了就是3-13世纪泉州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的状况,从兴起、建设到在宋元海上交通贸易中获取核心地位。
在这期间,泉州的变迁归结为下面四个方面:第一是以“衣冠南渡”的名义发生大量的北方汉人南迁。引来最多北方移民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王潮、王审知兄弟创建的闽国;第二是在衣冠南渡后,北方汉人开拓了农业,泉州的区位体系经历了一个转型(从松散到随堂的分布广泛、组织严密),泉州“市”的实力放大,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泉州成为当时分合不定的“天下”的经济核心区;第三,唐以前,汉人选择福建这个气候条件与北方相近的城市迁移,但唐五代,产生了相对人口的物产不足问题,唐后期到闽国时期,人口大量增加,各种自然条件使得农业生产受到阻碍。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开始适应泉州靠海的地理环境“以海为田”;第四,地方政府和士绅合作的城建事业,适应商贸规模扩大而选择扩大地理覆盖面及“大都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
王朝的更替并不阻碍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达,但唐代要求对外合法化,贸易需要经过广州市舶司批准,广州的地方商业保护对泉州海商的压制,于是泉州知州上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1087年后,泉州的海上贸易得到认可,才获得区域自主权。并不是说处在边陲就与朝代周期毫无关系,其实正是由于边陲地位,才有机会自由生长。在后篇文化多元时代也提到,泉州比起中原,一些仪式典章和实践并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被朝廷、地方的特定文化冲击。这里便以宋元时期泉州地方政府对市舶祁风仪式和天后仪式为例。宋元时期的官方化,也充分说明了在商业社会的影响下,这些文化符号也被吸收。这样的官方“让步”其实是当年文化意义上官民互动的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边陲”所涵盖的自由生长特征与地方政府政府的主观“让步”,才有现在所看到的泉州多元文化的场景,尽管也许现在所保留的无法体现当初的繁盛。
第三章所阐述的边陲拓殖,从我理解上看不仅仅是疆土、地域的扩张,从中感受最多的应该是商贸、文化、眼界的拓殖。如果说这本书所述的是一个不繁荣到繁荣再到逝去的繁荣。那么我觉得前三章所讲的便是一个逐渐繁荣的过程。经过历史的轮转,文化风俗的延续,从朝代的更替而带动的政府职能引发的文化、经济、海上贸易等等。
正统的空间扩张
第四到第七章讲述明清泉州史,也就是泉州“繁荣逝去”的过程。明朝廷对泉州实行了“海禁政策”,除了商贸往来,还有对于思想观念的冲击。尽管后期有做出许多努力,但是“海禁”让泉州遭受了重创。明朝建立以后,与“内圣之学”相关的海禁、内部绥靖、社区教化政策得以提出并实施,使得宋元发展起来的“官商合营”航海贸易遭到了打击。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政权从“传统国家”向“绝对主义家”转变的时期。从书中蒲氏家族的兴衰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商在这一转变中的命运。
第五章“正统空间的扩张”关注明清时期的文化统治状况。在理学官方化影响下,泉州的仪式和空间象征都体现了天地人的和谐,并以此营造出朝廷意图中的正统。
“内圣之学”的官方化,是因为“城”和“市”的此消彼长现象。明以前城墙不严谨但“市”很繁盛。明以后城墙坚固,但“市”的功能削弱,泉州从一个比较自由的边陲城市变成了国家监控的地方社会。“城”不单是指强制性的控制,还有文化内涵的教化,就是上面提到的“内圣秩序”,因此朝廷在城里设立铺镜制度,让民众共享朝廷欣赏的雅文化。宋元时期理学之风盛行,一如在自序中提到的《世界货舱》,呈现了宋元时期泉州的繁荣景象,这些论文表述的地方研究对于理论思考的价值在于颠覆那种视近代西方文化为繁荣条件的主张,多数还从朝廷、官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入手加以解释。在泉州理学和民间文化关系复杂,放在“非正式制度”类别考察,视其为宋元繁荣的来源之一。明清时期的文化统治状况,重视用理学来促使全民服从于正统的理论体系,泉州基本是处于理学霸权的时代,因此人们思想被禁锢,文化逐渐失去色彩,宋元时期泉州的,无论是商贸或是思想,其辉煌与繁荣逐渐消失。作者提到摩尼教被民间当做“佛”来崇拜,充分说明了理学容纳的“佛”已经取得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宋代的儒学是主要是在学者之间传播,明代的儒学主要是朝廷和官府组成的内在因素。不同时代的儒学作用也不同,“内圣之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
官方的理学还被用于城市空间的再设计和再解释,理学家的设想中秩序是天地人“三才”的自然联系,在理学官方化之前,建筑空间其实就有所遵循。泉州城这一空间的宇宙观传统不是到明朝才运用,而是在唐中叶建城始就遵守的。五代到元朝泉州大规模拓城,才使得泉州及其不规则,从这一方面看,与理学的天圆地方的对称性、一致性、轴向性的特征不一致。
即便从表象上看到与“理学”所持观念脱节,但是官方创造出一套空间象征语言,来发挥利益的作用,获得正统内涵。这一论点在明清的方志中,从泉州地理划分的五个部分来体现。从五个部分看泉州地图,它与太极图的基本结构相似。同时泉州的空间象征也强调帝国的“分野”系统(分野建立在三个系统之上,一个是州立系统,一个是行星轨道十二站和十二地支相类的系统,一个是地界二十八区与天界二十八宿的系统)这就包含了理学所说的宇宙观,进一步强调了二元结构,即“内”与“外”的程式化辩证关系。
除了“内”与“外”,泉州城空间还存在“上”与“下”的关系。“上”代表着帝国象征与统治,“下”代表着地方社会。作为连接点,类似于城门、城墙一方面是两个空间的连接,另一方面也象征着皇帝、官员、百姓沟通的渠道,这些媒介是试图强化等级与秩序严密强权的工具。除此之外,泉州作为整体还通过一个特殊的,用来与外界、上、天、山脉、国家交流的媒介——坛,包括社稷坛、山川坛和厉坛。山川坛代表皇朝的“自然君权”,社稷坛代表国家,厉坛则是惩罚的戒律。城门和坛这两种媒介说明了城市与帝国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帝国同时的建立和确认。
为了让正统更加正式,朝廷以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按照传统规范设计官方仪式的体系。书中列举了泉州祠、庙、坛的组织情况以及祭祀的详细情况。无论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还是包括山川、河流等五个部分、以及数字、方位、建筑的指代,都是通过仪式和空间的象征,来营造朝廷意图中的正统。
风水传说的真相
第六章“风水传说的真相”以周德兴的风水传说为切入点,论述了“海盗”、移民等明清时期泉州人对海禁高压政策的反叛。
故事将泉州的繁盛归结为风水的作用,后来又将城市的衰弱归咎于皇权的破坏,最后以讽刺形容了皇权在这座城市中压制地方发展失败的后果。故事与历史的真实性无法考究,其隐含的政治讽刺,与海上商盗的实际行动确实存在,也体现除“官逼民反”的性质。闽南沿海的商民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进行走私活动,朝廷虽用各种手段来镇压,商盗势力已在恶劣的环境下实现了集团化,有着强大的团队精神,朝廷的但财力不足守卫松懈,致使防卫都无济于事,官府自认营造了的理想社会面临大批海盗集团的侵袭。明清时期市舶官商制度已经沦落,商贸被视为非法,政府在农业资源匮乏的区域实行重农政策,这些都道是元代以后泉州地区商业上的局限。明朝对泉州采取强制性的控制政策,导致海盗猖獗、百姓移民,其实风水传说中隐含着一种反叛式的精神。
前三章读到了宋元时期的港口商贸发达,文化多样,此后开始便从蒲氏家族的兴衰影射出了泉州城的兴衰,第六章已是繁荣逝去的过程。前六章在我看来是个枝干,将泉州的发展背景从内到外,自上而下的多维度介绍,后面的几章会是很有意思的点缀。标题所提及的内容似乎带着神秘的色彩,许多涉及的仪式、传说等在闽南是极常见的,也许透过书本的解释与阐述,辅以田野的所见所想,会有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