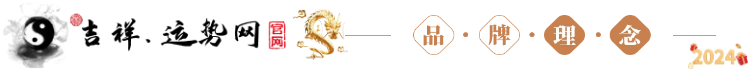王敬雅

《紫禁城建筑之道》,王子林著,故宫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01页,260元
我们现有的文物建筑研究,多是一种对于既定历史现象的解释,这也是我们一般研究理解文化遗产的路径,即一种现象解释学。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现象,然后去反思这种现象的成因。我们看到了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就会解释,这个黄色是五行之中土的颜色,代表天地之中;红色则是火的颜色,火可生土。之后,我们还会为其赋予现代人的理解视角:红色和黄色是原色,这种搭配会让建筑看起来更加庄重纯洁。
当然,这种解释方法是符合我们认知的基本路径的,因此也是现在物质遗产研究中常用的叙述逻辑。但是我们发现,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文化之外的物质遗产——例如庞贝古城、巴黎圣母院,这种叙事方式快捷方便;而对于那些我们自己文化基因所培育出的物质遗产——文物和建筑,这种解释方式便尤有未尽。
回到一个物质文化现象诞生之前,站在文化的原点上去重新理解它,成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故宫博物院王子林老师的新作《紫禁城建筑之道》便是这样一部作品,本书的主旨,不仅仅是回到元大都的那片平地上,去重新搭建一座紫禁城;也是回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原点上,从观念上复刻一座紫禁城。
一、天人沟通的通道
建筑和所有人类文明的产物一样,首先本自一种自然物观的认识。《道德经》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物”就是自然规律之“道”,我想也是本书所言“紫禁城建筑之道”。建筑的本质是人的栖居之所,《黄帝内经·素问》曰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居空间也就生成于“天地”“四时”和“阴阳”互根转化的规律当中,《黄帝宅经》则更是有很明确的论断:“宅者,乃阴阳之枢纽。”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者,紫禁城在中国古人对于风水的依附上做到了当时的极致。之前的研究,我们倾向于将建筑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研究造成这种事实的成因,而不把它当成一种文化现象,去解释文化堆砌和叠加的结果。在本书中,作者为大家揭示了紫禁城肇建的“龟蛇”布局、玄武之象、北斗之数、阴阳运用、山水之局。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这些建筑布局上的解释很难找到文献上直接的佐证,需要作者大胆的假设和细致的论证,而论证过程本身,就是对紫禁城营建思想的进一步探讨。
谈及中国古代建筑,风水学总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对风水学的敬畏反映了人类对脱离可预知的因果最深处的无奈,比如明孝宗在万岁上建了一座毓秀亭,之后公主夭折,清宁宫被火,故言建亭之举动坏了风水,主张建亭的大臣李广畏罪自杀。这三个可能没有关联的事件,被强制关联在一起,以便可以解释前两个不幸的发生。如果不幸变得有迹可循,那么多少会给当事人带来安慰,并消减对于未知的恐惧。
比如孔子对于天命的感叹,多数是发生在他对人事的绝望中,尤其是对生老病死的无能为力。颜回在去世时,孔子疾呼“天丧予,天丧予”;子路在去世时,孔子则说“天祝予”;冉伯牛病重,孔子说“命矣夫”。在这些人力无法预知和阻挡的自然事件发生后,我们急需一个心理慰藉,以证明世界的运行还在一个因果序列当中。
不过中国的神从来不是一种脱离了人类关系的、形而上的存在,他们存在的价值和土壤,就是解释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为之后的联系作出预测。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皇帝的特殊位置:一方面,不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他们从不宣称自己是一个超越了人类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承天景命”,成为神在人间秩序的代言人,以天道行人道。所以,皇帝所居住的宫殿,也正试图以一种具象化的语言,来表达皇帝在天人之中这种特殊的地位。
二、具象化的思想
以建筑表示天下秩序,并非儒家独有,正如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的设计一样,建筑是人类想象中可以与天、神沟通的媒介。现代住宅的局促,把我们每个人都关到了盒子一般的单元楼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们对建筑本身的想象力。而如果将这种场景还原到皇帝的住宅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去感知建筑与人的关系,去理解人以场所为媒介,向更高层次寻求沟通的尝试。
每个在建筑当中的人,都会有对建筑的设想和要求,有些是成系统的,有些是非常零散的。在有系统建筑想象的人中,有些人有强烈的愿望将其付诸实践,在紫禁城居住过的二十四位帝王中,这样的人有两个:明代的嘉靖皇帝和清代的乾隆皇帝。

嘉靖皇帝

乾隆皇帝
作者在书中对可以代表这两位皇帝的建筑,都做了详尽的描写,探究了这两位皇帝的思想源流,并具体分析了这些思想是如何体现在建筑中的。
明代嘉靖以“礼仪”为武器,在政治斗争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其中明堂的兴建和对其生父的供奉是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建筑本身已经脱离了最基本的“美观、实用”的要求,而需要展示出一种现实的象征意味。
现在中正殿区的明堂建筑,以建筑形式彰显礼治地位。明堂最初的形式,是天下秩序的缩影。“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三公、诸侯乃至九夷八蛮,各有所处。故而“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
嘉靖皇帝利用了这一政治意向,在中正殿区建造了“亞”字形的玄极宝殿建筑群,并以此地祭祀其生父(第161页)。这种建筑上的表现有很多共通性,明堂所要表达的内核,与佛教的坛城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即以方寸之地,表现出世界的秩序。这也为后来隆德殿改建为藏传佛教的中正殿奠定了基础。
乾隆皇帝以各种场所实现自己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这无疑是其精力旺盛的一个佐证。乾隆时期几乎对宫中所有宫殿都进行了重新装修,有的进行了改造,有的添置了匾额,有的则对室内空间做了重新分割。
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乾隆皇帝做这座城主人的时间是最长的,他的政治生命以一位备受皇祖宠爱的皇子为始,以一位高龄期颐禅位让政的太上皇为终。而这两端,又都反映在了乾隆皇帝对紫禁城建筑的改造上,即重华宫和宁寿宫二区的重建(第187页)。
古代人自明的方式十分有限,我们今天可以改微信签名,发朋友圈、发微博。但乾隆的自明方式就没有这么丰富了,除了每天写诗或发上谕,没有更为直接快捷的方式将他的志向或是性格外化。但是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有表达欲望的人,也就促使他一方面大范围将宫殿改名以自明其志,一方面改动建筑格局以表现他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
以清代皇帝来看,能做到有始有终的,仅有乾隆一人,能做到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全面铺开的,也仅有乾隆一人。
当然,这种具象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有时也是某种特定的行为风格。雍正移居养心殿,帝国的运转更密集化了。定制化的宫殿居所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皇帝的日常消耗,所有的目标就是让他高效地运转起来。因为在雍正的理念中,一个好皇帝,在生活上应该是被虚化的。
三、权力的场域
如果把皇宫当成一座影城,这里上演的戏码,一定是围绕家国分野、权力斗争的。《周礼》中对于宫殿的最初设计中心,就是标定与天子相关的各种势力场域界定。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三朝五门之制,即“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门内者,或谓燕朝”,其实表现的就是皇权逐渐扩散和外延的过程。
因此,乾清坤宁除了是宫殿的命名,更标志了建筑的政治意义,“朕之正寝”(第108页)的讨论,远非皇帝要在哪里起居饮食那么简单,而是纲常伦理的物化反映。
以六宫的设计为例,乾隆十三年(1748)到十四年间,东西十二宫被各自配装了旨在反映后宫嫔妃恪守妇德、温柔恭顺的匾额。并奉谕旨:“此十一面俱照永寿宫式样制造。自挂之后,至千万年不可擅动,即或妃、嫔移往别宫,亦不可带往更换。”(第114页)
这十二方匾额,连同布置在宫内的宫训图,打造了一个强力的话语场,在这个场域之内,嫔妃只是按部就班地被安排在她们各自的位置上,像机械上的零件一样参与帝国的运转。她们个人的生死荣辱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在一个侧面说明,机械化已经深入到皇帝的私人领域,连他自己的后宫,都被严格地组织化了(第116页)。所以,现在我们理解慈禧太后对于六宫的改造,不仅是一种生活空间上的改建,也是一种心理空间上的破除。
如果说嫔妃完全属于皇权的依附,那么这种政治斗争在建筑上的体现,以太子宫的兴建最具代表性。明清两朝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有很多互相角力的势力,如外官与内侍,皇权与相权等,而皇帝与太子,也是这样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势力。作为皇帝,一方面希望太子可以能力不凡,继承国柄;另一方面又害怕太子势力过大,威胁皇权。在这种角力的过程中,太子宫就成为了权力外化的场域。
天子有五门三朝之制,太子则有三门一朝之制。太子宫的营建将皇帝和太子这种既是父子亲缘、又是权力继承的复杂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太子于皇帝之东,属于大的紫禁城结构的一部分,从属于整个皇权体系。另一方面,太子又有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和话语象征系统,这与嫔妃不同。他不是一个完全依从于皇帝的附属品,并且与皇帝之间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简单来说,现任皇帝多在位一天,太子就少在位一天,这种冲突和矛盾,在皇权至上的明清社会,显得格外突兀(第241页)。
乾隆八年(1743),随着乾隆皇帝的立储计划破灭,太子宫的计划一度被搁置。而到了乾隆禅位后,这里就成了乾隆皇帝与其继任者——嘉庆皇帝权力交接的现场。嘉庆元年,新皇继位,仍然居住在毓庆宫,而对此,乾隆皇帝的改建就别有深意了。“付忧与子讵忘付,宁寿斯身何敢宁”“自揣精力强健如常,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帝自图安逸耶?”话虽说得委婉而勉强,但是当有臣子真正将乾隆与嘉庆区别对待时,老皇帝便勃然大怒。
嘉庆元年正月,湖广总督毕沅上奏中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之语,只因将“圣主”与“太上皇帝”分别开列,便得了乾隆皇帝一顿斥责,并再次重申“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事务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乾隆皇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而嘉庆此时的表现也确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实习生”。《朝鲜李朝实录》中称其“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亦步亦趋之态可见。
在毓庆宫一直悬挂着乾隆皇帝对嘉庆的训诫之辞,其匾为“履道安敦”,下有联曰“笃学在躬行,宜循实践;淑心惟理顺,克务懋修”。这是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皇帝为嘉庆潜邸题写的。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旨下永琰为皇储,移居毓庆宫,这方匾额和楹联一并被移到嘉庆的新寝宫,并在接下来太上皇摄政的四年中,作为对于新皇帝的规训。
随着咸丰时期对于毓庆宫一区的改造,我们可以体会到,太子制度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废除,但在清代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而这种皇权内部的分割与整合,也一刻未曾停止。
结语
西方在研究建筑学时,通常要举出维特鲁威所作的《建筑十书》,他在书中强调建筑师的教育、知识的统一性,建筑的意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建筑与社会伦理、人类健康与环境等问题。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建筑师,应以学习哲学为途径,洞察自然物性和人生真谛,同时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恰当地设计建筑和装饰雕塑。
当我们再次面对自己的历史建筑时,是否也应将它作为一个知识的统一体来认识,注意到它其实是历史中各种要素不断叠加拼合的产物。
我们试着将紫禁城还原到肇建之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完全摒弃了正朔岁首的天象原则,而是根据“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理论来营建新的京城,这便是这座建筑的原点。
今天我们对古人布局上的见解,是根据文本而进行的反推过程,并不一定完全还原古人建城的真实意图。但是,这种反推正要回到历史建筑的原点,以一个设计者的身份,去还原当时人的认知体系和知识背景。因此,要求研究者按照孔子所言“叩其两端”,从现实建筑和设计意图两个方面去探索当中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解读和论证的结果可能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极致的。不过从作者的研究经历来看,对于“紫禁城建筑之道”的探讨,正是这样一种不断推进的过程,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